
老包头走西口历史文化街区传统民居精致的砖雕。
包头方言的多元文化特点
作者/胡云晖
包头方言是在“走西口”这一特殊历史的大背景下孕育形成的地方方言变体,与其他地区方言形成的模式完全不同的是,它并不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步演变而来,而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加速形成的。
这是因为包头及其周围的广大地区,一直都是北方少数民族休养生息之地。即使在“走西口”初期,也一直是蒙古民族的游牧地,汉族民众以“雁行”的方式春来秋回,缺少形成定型方言的必要因素。其后,随着汉族移民的大量定居,移民村镇如雨后春笋般兴起,萨拉齐、包头等大型城镇渐成规模,农业垦殖如火如荼,商业活动日益繁盛,包头地区由自然地理上的阴山锁钥,一跃而成为塞外通衢,人口规模日新月异,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从而为包头方言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但这一过程,最多也仅有二百多年的时间,包头方言的真正整合完成,更是较为晚近的事情。
“走西口”,是一场波澜壮阔的社会大变革,在包头地区这一特殊的表演舞台上,诸多民族、各地移民、各种经济形式、众多重大历史事件,如走马灯似的在极短的时间里,轮番交替出场,错综复杂,让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包头方言正是在这种极为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中,通过继承保留、融合吸收、淘汰创新等方式整合而成的一种有别于晋陕方言母体的新方言,以其鲜明的多元文化特色而独树一帜,别具一格。

老包头走西口历史文化街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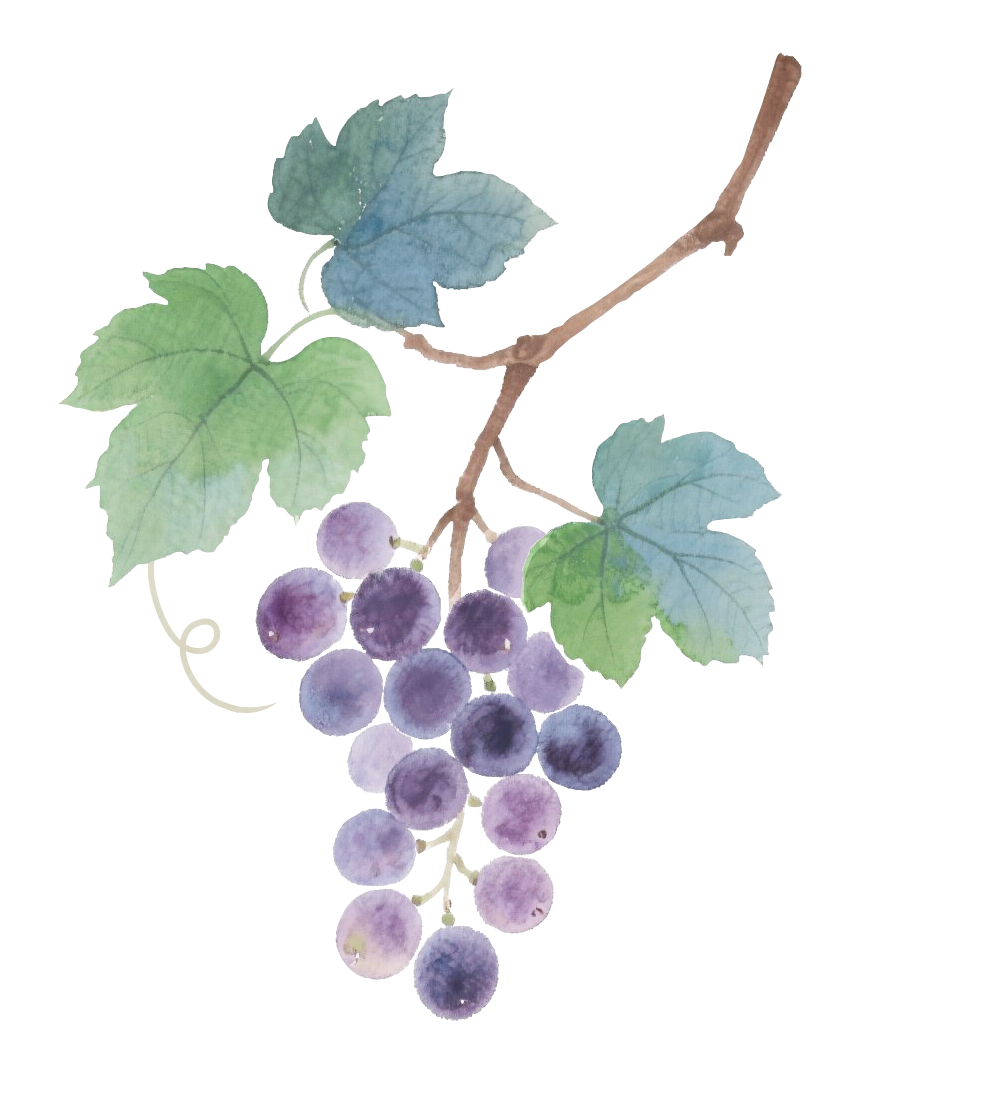
包头地区最早的汉族移民,多来自山西、陕西等地,当时,各地移民所操方言五花八门,各不相同,往往影响正常的语言交流。但各地方言中遗存的古汉语成分,却具有通语的性质,可以被大家普遍接受。因此,也就非常自然地得到了保留和继承,这是包头方言相较于山西、陕西母语方言更多存古的主要原因。
包头方言的存古,有下面几个特点:
1、保留了入声音调。古代的入声字,在包头方言中绝大多数还读入声,甚至一些舒声字,还转读为入声字,古代的入声调,在包头方言中不仅没有削弱,还得到了发展。
2、保留了许多古音,如古代舌上音读作舌头音的语音现象,普遍存在,例如宽绰发音为宽淘,舒畅发音为舒傥,宽敞亦发音为宽堂,心促胆跳发音为心毒胆跳,悉知尽明发音为悉底尽明等。
3、继承和发展了古代的分音词现象。诸如不浪(棒)、骨拢(滚)、黑浪(巷)、不烂(绊、拌)、骨拉(刮)、秃论(褪)等,不仅分音词的数量极大,而且对分音词的使用形式有所发展,创造出了丢跤跌骨拢、脱叾论胯、钻头觅黑剌、拨脚不烂手、脚踢手不剌等多种形态的分音词词汇。
尤其在词汇方面,保留了大量的古语词:
1、古语单字的大量保留。如称肿为胮、藏匿为寄、到为至、找为寻、玩为耍、什么为甚、带领为引、依仗为傍、擦拭为搌等;又如啖、扽、唾、庹、缀、粜、滗、嗾、拙、诌、掫等,具有古汉语语义的单字在日常话语中触目皆是。
2、古语词的频繁使用。在包头方言中,许多频繁使用的词都可以在古代典籍里找到依据。譬如包头方言指草树丛聚处为薄子,如:草薄子、树薄子、圪针薄子等。薄音八,入声。此词早见于先秦时期。《楚辞·九章·思美人》:“解萹薄与杂菜兮,备以为交佩。”洪兴祖补注:“萹薄,谓萹蓄之成丛者。”又《九章·涉江》:“路申辛夷,死林薄兮!”王逸注:“丛木曰林,草木交杂曰薄。”《淮南子·俶真训》:“鸟飞千仞之上,兽走丛薄之中。”高诱注:“聚木曰丛,深草曰薄。”《文选·宋玉〈高唐赋〉》:“薄草靡靡,联延夭夭,越香掩掩。”刘良注:“薄,草丛也。”近人章炳麟(太炎)《新方言·释植物》:“《说文》:‘薄,林薄也。’平阳一树亦称薄子。薄读若博。”因草树丛聚处多低凹,故包头方言转指低凹处为薄子,又曰薄洞。通常多写作卜子、卜洞。又譬如萹竹竹,是乡间常见野草名,农民多充做猪草,即萹蓄。《尔雅·释草》:“竹,萹蓄。”晋郭璞注:“似小藜,赤茎节,好生道旁,可食,又杀虫。”《说文》:“萹,萹茿也。”梁陶弘景《名医别录》曰:“处处有之,布地而生,花节间白,叶细绿,人呼为扁竹。”又包头方言称地震为地动,所说为古语。《尸子》卷下:“海水三岁一周流,波相薄,故地动。”《吕氏春秋·音初》:“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漯水》:“昔邑人班丘仲居水侧,卖药于宁百余年,人以为寿,后地动宅坏,仲与里中数十家皆死。”其地动,皆指地震。而宋元以来文献中所习见的词语,在包头方言口语中更是举不胜举。
3、杂以文言虚词。方言中使用文言虚词,虽然已没有了频繁的之乎者也,但仍然有少量的残存。如以当无然、枉徒然、未之谅、公之匀之、十之八九、何其苦、无其数等。其中的然、之、其,就都是文言虚词。此外如不外乎、不惧乎、不虑乎、不惮乎、不离乎、不在乎、全乎、惬乎等,乎字的这种用法在文言中也极为少见,很可能是受文言的影响而变异产生的。
此外,包头方言还保存了许多不为普通话所继承的古代成语。这些成语表达能力都很强,在历史上曾频繁使用,现在已逐步为人们所忘却。而包头方言却给予了大量的保留,如碍口识羞、安安顿顿、安然无事、拨草寻蛇、白说六道、白面书生、搬唇递舌、半死不活、半新不旧、不当不正、愁眉泪眼、攒零合整、寸步不离、赤贫如洗、大马金刀、顶缸受气、冬年节下、逢人至人、穷身泼命、七病八痛、揉眵抹泪、失惊打怪、剜墙拱窟、忘恩无义、小眼薄皮、一还一报、一棺一椁、远路劳神、贼打火烧、指猪骂狗,等等,数量非常之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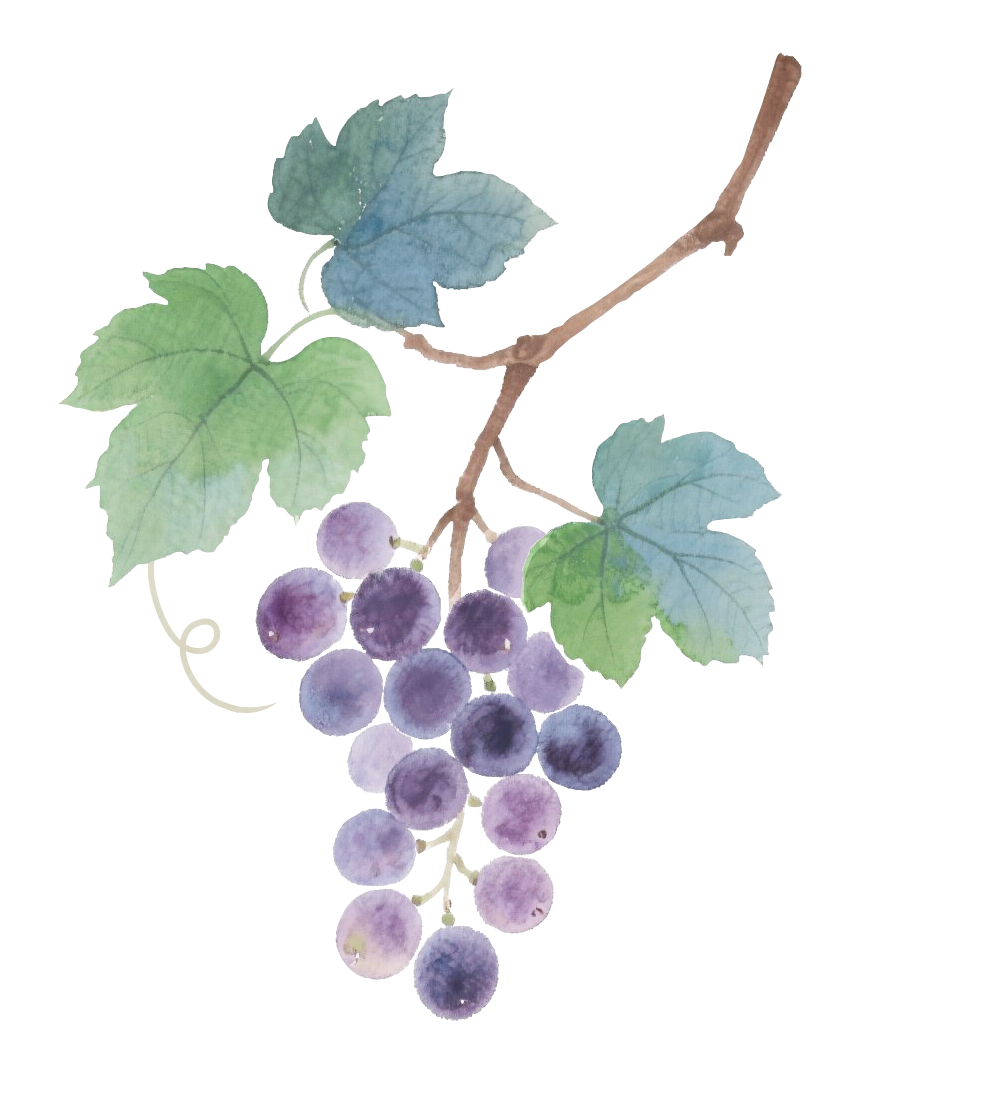
“走西口”进入包头的,主要是山西移民,他们来自山西省的不同地区。不论是垦殖时期“跑青牛犋”的农民,还是包头成为西北皮毛集散重镇后做买做卖的晋商,他们的纷纷而至,使富有强烈地方特色的山西不同地区方言也随之而来。当时的包头,物攘人稠,三百六十行,南腔北调,各说各话,一片山西各地方言大荟萃的景象。而且,最初在语言交流中遇到隔阂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之后,为了交际的需要,人们都自觉不自觉地舍弃了自己方言中那些过于狭隘的部分,保留和追求通俗与大众化的部分,经过长时期的磨合,最终,一种为大家普遍接受的方言交际语形成了,它不是山西方言的某一个,而是山西各地方言的融汇,是一个包罗万象的集合体。这种集合体,本身就具有多元文化的特点。
首先,包头方言存在着明显的内部差异。
关于包头方言的形成与内部差异,旧志书有过明确记载。民国《包头市志·风俗志·语言》曰:“包市五方杂处,语言极不统一。除蒙人用蒙语外,汉人亦有熟悉蒙语者。至于汉语,则方言不同。四乡居民,由河曲移来者最多,故河曲话为最普通。至于市城,则忻县、定襄、祁县口音为多,又杂以太谷、府谷语言,统谓之山西话。”民国《萨拉齐县志·礼俗·方言》则说:“汉蒙回杂处日久,濡染已深,所操语言,胥无隔阂。汉多晋商,半近晋音。蒙年长者,亦谙蒙语,惟不习用。本邑语系,属北方官语,故方言限于一隅。”
《绥远通志稿》也曾经对内蒙古西部区汉语方言的内部差异问题有过极为详细而中肯的论述:“各县汉人,其始均属寄民,迨后渐变而为土著。所操语言,虽历年久远,其音调仍多含有原籍地方之成分。口外旧为五厅,即归、萨、托、和、清是也。今稽其城乡大户历世较久者,则多为晋北各地人最初占籍之户。故其语言,虽略有不同,而大体不出晋北各州县之范围……萨县城乡语言较劲直,原籍亦以忻州、定襄为主。晋之中部如祁县、寿阳等处者,亦有之。故全县乡村语言,有与忻、定相同,迄今未稍改易者……武川与归绥乡村为近,包头与萨县为近,惟武、包较归、萨发音又高吭矣。固阳与武川、包头连界,而语音则与包头相近,惟语音较低缓耳。大约各县语言,以萨、包一带为语急而音洪,其民俗亦特为刚劲也。安北人民,以晋陕沿边及省境山前各县者各居其半,语言仍近乎萨、包……由归绥而西自萨、包,北至武川、固阳,其语音完全以忻、代、崞、定为主干,再西则参以陕边之音……故除中部如归、萨二县外,其他各县,殆各因其接近之地,语音随之而变。惟归、萨其初不与内地相接,故其语言亦难以一地名之,盖混合忻、代、崞、定而成为一种特有之土语。是则以归、萨语言代表本省之语言,亦无不可也。”其中所说的各地的语言差异和特点,至今改变不大,所谓“混合忻、代、崞、定而成为一种特有之土语”,说的就是具有多元文化特点的方言集合体。
在20世纪三十年代,一些受山西各地方言影响而形成的方言内部差异已经在一些地区固定下来,所以《绥远通志稿》中又说:“托县语音,亦有与他县特殊者,如谓光为刚、黄为杭、外为未、双为伤、拐为鬼、快为跪、赔为牌、装为张。和、清两县语音亦多与托相近。归县四区毕镇一带,则黄为禾,王为倭,窗为搓,忙为磨,张为遮。萨县则与归县乡音为近,皆源于晋之忻、代、定、大同口音转变而成者也。”
其中所说的语音现象,现在在这些地区依旧存在。如土默特右旗沿山区美岱召镇一带居民,将韵母ang,发音为e,韵母为iang、uang的字也相应发生变音。如厂,发音为扯;上,发音为社;仗,发音为这;壮,发音为坐;创,发音为错;爽,发音为锁等等,与其他地区方言发音明显不同。对此类语音现象感到好笑的其他村落人,还专门编了一段话取笑他们:“从南上来一群狼,尾巴丈二长,当啷一枪,打住一只羊。”
又如土默特右旗苏波盖乡东老藏营村村民,其祖上多来自山西忻州地区,所操语言有明显的忻州方言特点,除韵母为ang、uang的字,与上述地区相同外,韵母为iang的字,则发音为ie。如羊,发音为爷;想,发音为写;讲,发音为解;抢,发音为且,等等。这与其他地区的方言又有明显的差异。
与山西方言内部存在着较大差异一样,包头方言也存在着较大的内部差异,所不同的是,山西方言的差异反映在较大的区域上,是以市县、地区为界的,而包头方言的差异区域却要小得多。如在土默特右旗,黄河沿岸与沿山区之间,一个村与另一个村之间,都存在着语音与词汇的差异。形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些地区的居民,其祖先“走西口”时来自山西的不同地区。这些早期的山西移民,翻山越岭、长途跋涉来到塞外,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为了互相帮助和易于交流,通常是以同乡的形式聚居的。而随后“走西口”来的移民,也多是投亲奔友。这样逐渐形成的村落,其居民往往就纯是山西某地的移民,所操方言,也自然是那个地方的方言。一个村与一个村的居民构成不同,其方言有差异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包头地区历史上形成的移民村落中,就有许多类似的同乡村,如榆次营子、五台营子、寿阳营子、祁县营子、繁峙营子、定襄营子、崞县营子、忻州营子、代州营子、武乡县等。仅从其村名,就可以推知其最早的居民构成,山西老家方言对他们所操语言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其次,包头方言对同一事物的表达,具有多种词汇并存的现象。
包头地区的人口由于来自山西的各个地区,在语言交流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要把自己特有的方言词汇融入大包头方言之中。其结果就使得表达同一意义的方言词汇存在多种说法,形成了包头方言词汇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例如公驴,既称“叫驴”,也称“叫嘎子”;豆角,既叫“豆荚荚”,也叫“莲豆”;麻雀,既叫“老家贼”,也叫“老家巴子”;车前草,既叫车前前,也叫车串串;伯劳鸟,既称“马伯劳儿”,也叫“虎伯劳儿”;蒲公英,有叫“姑姑英”的,也有叫“拨灯灯”的,也有叫“婆婆丁”的,还有叫偷针婆婆、偷针媳妇儿的;蟋蟀,有的叫“蛐蛐”,有的叫“秋蛉儿”,有的则称之为“黑嘶儿”,等等。称谓方面,即使同在一个村落里,称呼父亲的弟弟,有的叫叔叔,有的叫爹爹,有的则称之为伯伯;称呼伯父的妻子,有的家族叫大妈,有的叫大娘,有的则称之为大大。一般词汇方面,更是纷繁复杂,或者同义,或者近义,其细微差别,非熟知方言者,不能体会和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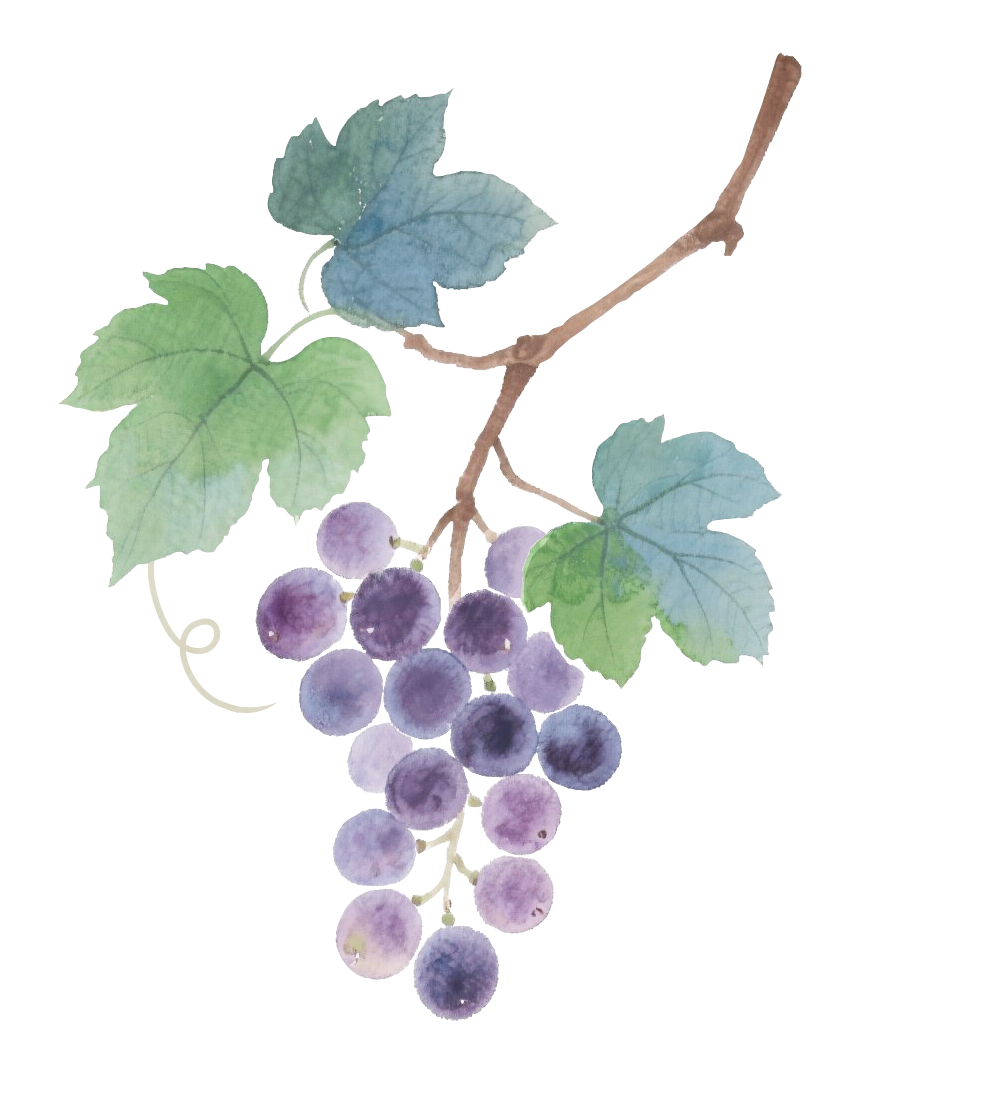
蒙古语词被吸收进入汉语,大约在宋代即已开始,尤其是元朝时蒙古族入主中原,蒙古文化极大地影响了中原文化,蒙古语词进入汉语尤为普遍。翻开元明戏曲,不论是道白还是唱词中,蒙古语词的使用屡见不鲜。可以想见,当时日常生活语言中蒙古语词的使用可能更为频繁。包头方言是继承元明清古白话而发展形成的,所以自然也继承了其中所吸收的蒙古语词。如称杀为哈喇、突然为忽喇巴、聊天为倒喇、贼为忽拉盖、走为牙步等皆是。这些蒙古语词并不是在“走西口”之后受当地蒙古民族语言影响才进入包头方言的,而是山西移民直接从中原官话中带来的。由于包头蒙汉杂居的自然条件而进一步得到强化,所以它的使用频率要比其他方言更多一些。
更多的蒙古语词进入包头方言,是在“走西口”之后。走胡地,随胡礼,移民因为要跟世居的蒙古人打交道,垦殖、经商,就必须懂得蒙古民族的语言和风俗习惯,通过不断交流与共同生息,耳濡目染,许多蒙古语词自然也就成了当地汉语方言的一部分。历史上包头方言中蒙汉语词混杂使用的现象非常普遍,许多“二人台”小戏的道白,常常掺杂有蒙古语词,形成了所谓“风搅雪”的语言形式。
包头方言吸收蒙古语词的形式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直接利用蒙古语词指称地名。如哈林格尔、北只图、海流图、杨圪塄、公忽洞、全巴图等,是纯粹蒙古语词;马莲淖儿、大脑包、壕赖沟、二楞滩,是蒙汉合用词。
2、用蒙古语词做人名。如憨叭儿(狗)、毛脑亥(赖狗子)、查汗呼(白小子)、把得儿呼(好汉)、吕台吉等。
3、其他蒙古语词借词。此类词语在包头方言中数量很多,有的是常用词,有的只是偶见使用,如打不素(盐)、稳塔(躺下)、五圪胜(死亡)、嘎亥(猪)、耳直更(驴)、达啦嘎(长官)、淖儿(海子、湖泊)、抹奈(我的)、塔奈(他的)、讨劳盖(头)、抹了盖(帽子)、脑亥(狗)等。
蒙古语词的大量吸收,不仅丰富了包头方言的词汇量,同时也使包头方言具有了明显不同于山西方言的地方特色,从而确立了其在晋语中的特殊地位。
此外,包头方言中还吸收了其他少数民族语言词汇,如藏语的召(召滩、召拐子、召墙、召地等)、道尔吉(愣道尔吉)、喇嘛(小喇嘛进了大召),满语的嘎喇达少爷(嘎啦达义为参领)、扎箍(满语义为治疗,方言转义为整治)、喇乎(马虎)、哈喇(食物有异味)等,还有一些与藏传佛教有关的词语,如七十二个沙不那尔、吹牛腿、跳神打鬼、莜面鬼、送八令等,都体现出包头方言文化多样性的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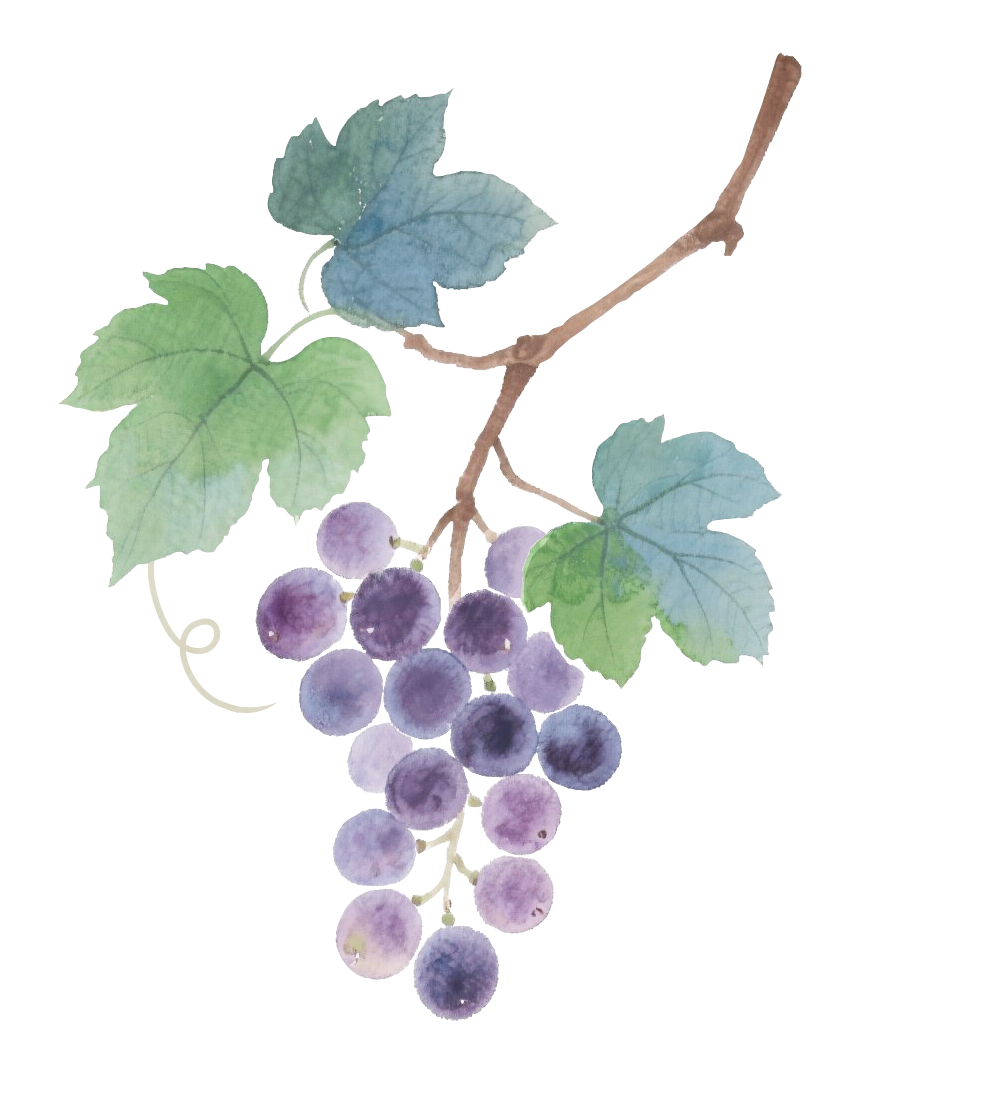
如上所述,随着“走西口”的不断深入,包头地区,尤其是老包头城,人口急剧增加,商业经济极度繁荣,车船辐辏,商贾云集,工商业形成了“九行十六社”,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各色人等,一时间风云际会,而对于那些走江湖、逛世路的人来说,自然是非常重要的码头。由于镇守官员轮番更替,封建军阀走马灯似地来去,使社会更加不靖,土匪蜂起,独立队、不浪队,名目繁多,一经招抚,摇身一变,又成官军;原系土豪,三相公、二少爷,杂色纷呈,拉起杆子,啸聚人马,就能立起山头。至于散兵游勇、哥老会、红枪会、乞丐帮,以及戏班、赌场、车行店脚牙、引车卖浆者之流,更是应有尽有,为江湖社会的形成,培植了土壤,奠定了基础。彼时的塞外包头,因为社会构成极为复杂,所以其社会语言也非常丰富,许多行业由于历史传承的原因及生存的必要,几乎都有自己的隐语行话,方言谓之“黑国语”,而流传全国的江湖话在包头城区也非常盛行。
这些隐语行话和江湖话,作为一种行业、帮会语言,具有极为强烈的封闭性,但在长期的交际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有一些词语就进入了方言系统,成为了包头方言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
例如称受伤为挂花、挂彩,称踩点为踩盘子,称绑票为请财神,称走为扯活,称匕首为七子,称形势危急为风头紧等,就都是来自于土匪黑话。《绥远通志稿》卷五十《民族(汉族)·语言类·方言俚语》说:“各县指结伙行劫者曰独立队,绑票勒索曰请财神。匪中类多隐语,以掩耳目。其最通行者,如谓官军来捕曰水洪,受伤曰挂彩,子弹曰鱼子,暗报官军曰改水。”这些隐语为大众所熟知,丧失了隐语的隐秘性,最终就成为特殊的方言词了。
又如方言称讨吃货为道啃子,称看为扳沙,是来源于理发业行话;称傻子为壁龛,是来源于戏剧行话;称妨主货为白头牛,是来源于哥老会行话,等等。这些词语的进入,极大地丰富了包头方言词汇库,增强了修辞表达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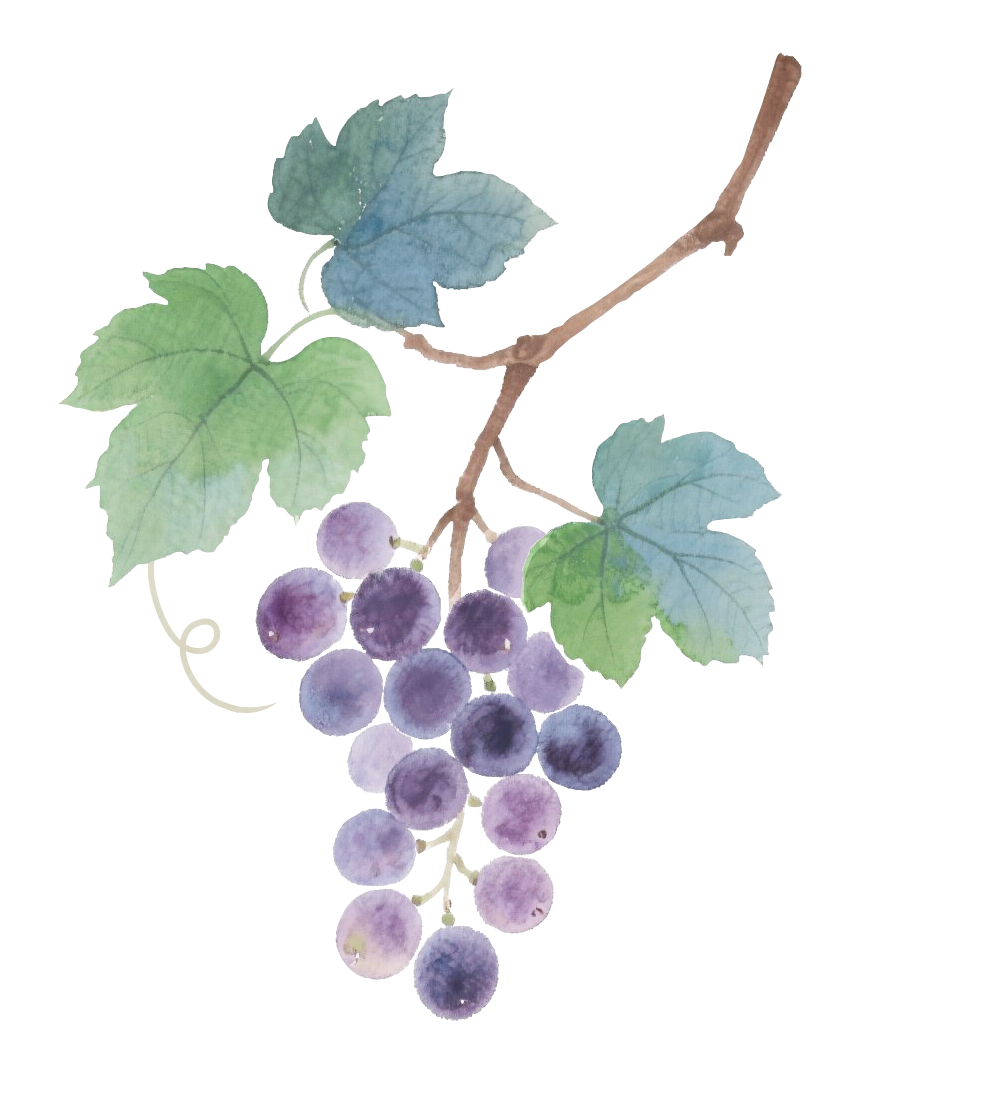
除上述几点外,包头方言的多元文化特点,还表现出极强的创新能力。由于在包头地区定居的山西“走西口”移民,既是来自山西省的各个地区,又在塞外经历的是一种全新的特殊生活过程,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一场对原有语言的革命。其中既有对传统语言的拆分和整合,又是新的语言的创造。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诸如公中、伙盘、牛犋、雁行、跑青牛犋、掏根子、拉骆驼、走草地等词语,就是完全不同于山西原有方言的新词。而且由于山西移民的进入,一些蒙古语词(例如地名、人名)也以汉语的表现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这无疑是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一种丰富和充实。在吸收了众多的蒙古语词汇之后,产生了蒙汉合璧的“风搅雪”语言形式,而且在包头方言俗语中,不仅有一般意义上的、具有地区特色的谚语、歇后语、童谣、谜语、绕口令、串话等等,还有隐语行话的大量融入以及别具一格的露八分语言。因为“走西口”而新生或发扬光大的许多艺术形式,如“二人台”“山曲儿”“爬山调”等,都为方言的成长发展提供了绝佳的展示平台,相辅相成,极大地丰富了包头方言的语音语汇,使其明显有别于其他的晋语方言。
所以说,包头方言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在继承和发展母体方言的基础上,受包头地区特殊的自然地理、人口构成、商业活动、经济发展、历史事件,以及其他明显有别于山西方言的诸多因素的影响,在方言语音,尤其是在词汇的创新、充实方面发生重大变化,在吸收了当地少数民族语言后,融会贯通而最终形成的具有“西口”特色的新方言,对包头方言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和剖析,对于研究包头地区的人文历史,发展包头地区的文化事业等,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编辑:吴存德;校对:霍晓霞;一读:张飞;一审:张燕青;二审:贾星慧;三审:王睿)

留个言再走呗...